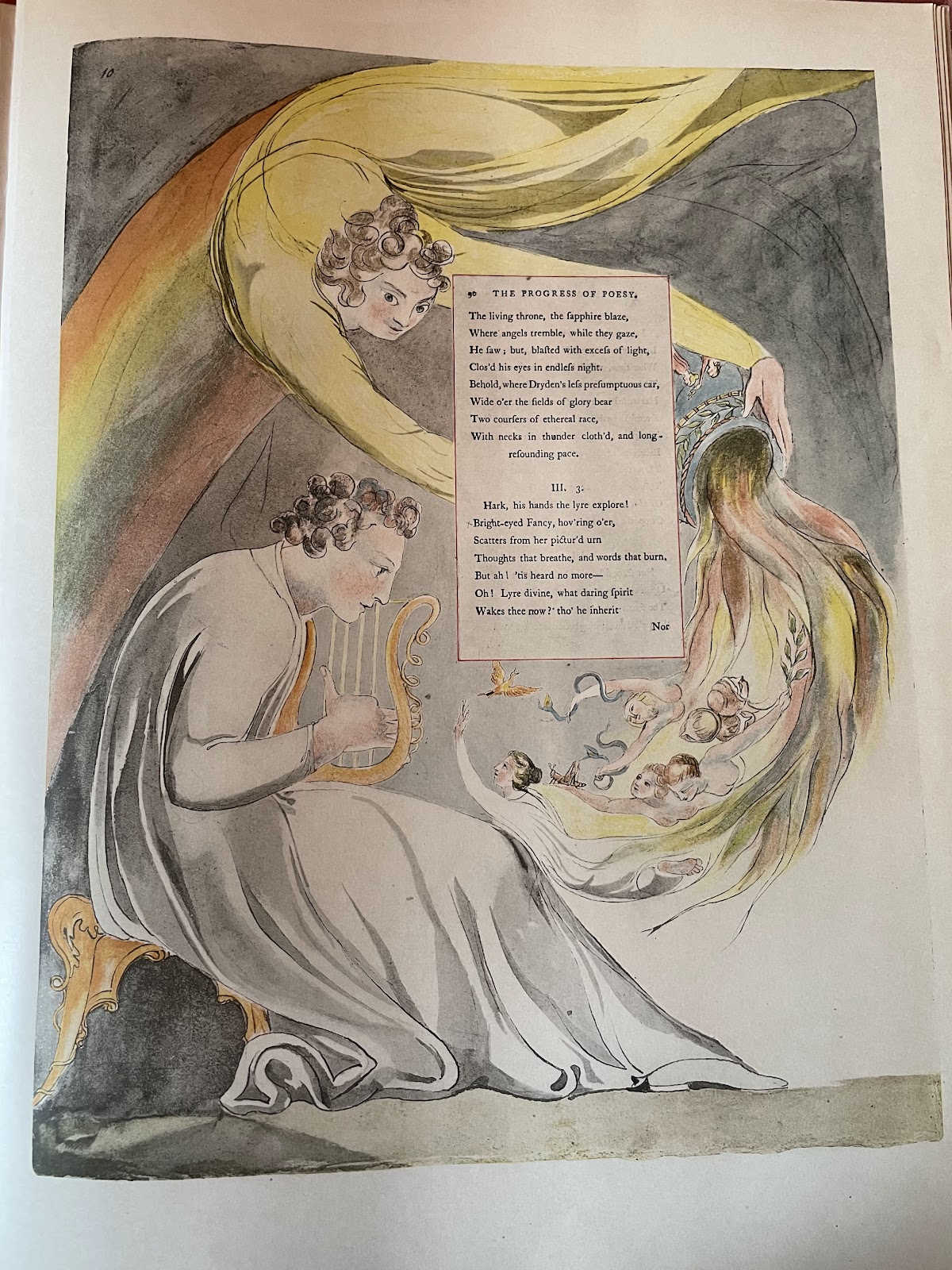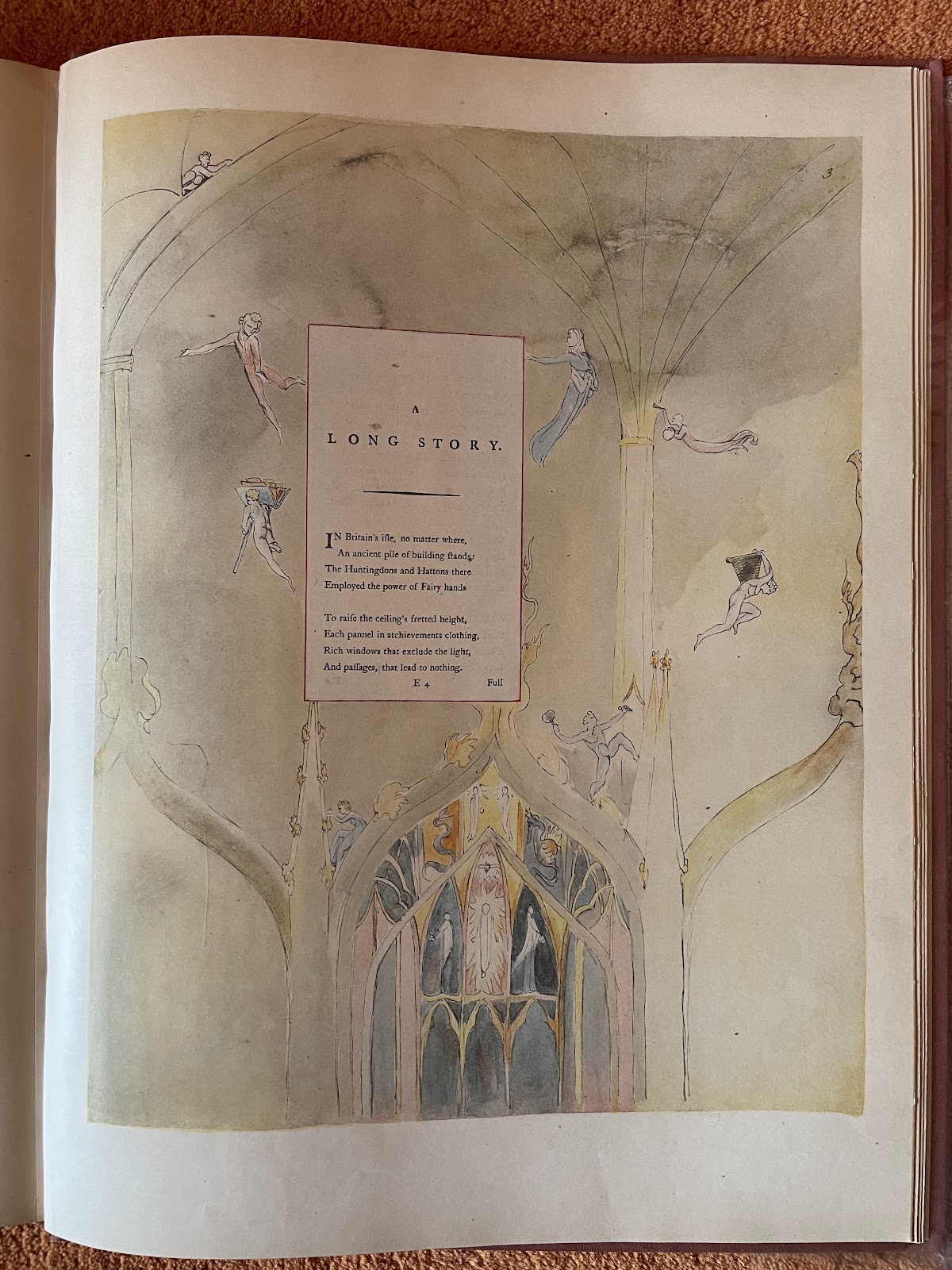Portal之為APP,主事者上山下海錄下世界秘境晨昏之間的大自然正音,免費可浸淫數境,一年付近五十美金則全境暢遊,且開放動態聆聽,隨著頭部的轉動,音場跟著移位,身臨其境。在試聽的一周內,急忙登上尼泊爾的高山Ama Dablam,到嚮往的蘇格蘭Isle of Skye閉目體會,轉到冰島聽火山口的能量,又拉到遠距聽地平線上的火山在大地中隆隆作響,或冰河的破裂傾壓;其他鳥語,麥浪,雨林,瀑布,柴火當然皆有,有地名有地點,有clip為證。
常常音樂聽到麻痹時,就進入叢林借獅吼蟲鳴、水的咆哮形成護城河——可是,一種卡卡感,猛獸異禽怎麼又叫了,更,叫個不停,讓浸淫感瞬間縮小,惱人地集中在意識前方,變成吵,干擾——loop的破綻——讓人跌出境外。
而Portal卻能讓人在英國花園的交疊禽音中渾然忘我地走完整條街,買菜,等車,看捷運/動車/bart各地的同行者溶入他們的手機沈浸在各自心與神的所在;禽音是那麼逼真,清晰,生動,位置性明顯,你自然望向清脆鳥鳴的來源,如果剛好看到一隻鳥,那就是它在說話,如果是車廂頂,也行,我聽得見的隱形美好天然是我們集體的穹頂,你我同在花園裡。
完美的線性前進中,又忍不住開始找loop的銜接點;突出的烏啼做定點,專注算著它多久之後再出現,才不過幾分鐘的音軌,還不及發現破綻,早走神於他事,回神欲重來,瞬間也忘了在專注什麼。
然後注意到樓下馬路上被紅綠燈節制九十秒一輪的引擎起步聲,每次因等燈號的車輛亂數組合而不同,但如果有這麼相同的一次,那,是否是一個loop的形成?
白噪音,環境中的眾聲交織。當收音麥克風遠離小溪、大海、瀑布、雷雨—水的主唱,火的燃燒,發音的禽蟲獸,朝向高廣開闊的大地,義大利北方與奧地利交界的大理石山峰Tre Cime di Lavaredo(Lavaredo的三尖峰),彷彿不變的一道長音,仔細中有無盡細節,來自陣陣大氣能量在群山中變速變向運動,搖撼植物與水製造聲響,大塊噫氣吐納,造形殊異的大地願做樂器,萬物齊聲號叫一地獨有的齊物聲形,不是白噪音,是遠古縱切時間的天籟。
如果留神,辨別出在表面跳動的變動聲音,在某一刻,一個極偶然的空白,上層音齊啞,屬於這個地表的基礎長音浮出,天使剛剛經過的靜默,地籟乍現,那一刻,是被冥冥力量控制編輯的一個周而復始的超級音軌・的・銜接點;或者是周卻不復始的單一loop的形成?
絕對有個loop,循環不斷的聲軌,配著不斷消逝的時間流,只是沒意識到而已。
安靜的夜晚,幾哩外高速公路的永恆車流進場,沿海灣的鐵道,今夜火車穿過平交道拉下鳴笛,巨型風琴按下B大調六音合弦,一聲又一聲,緊接起響徹九十年代涼夜的合弦尾音,好長好長的loop,心情列車進站又駛離,從人生未來是嚮往的謎到謎團破解,一段落差,此刻與過去串連的鳴笛,因此不得再循環。
似曾相識感,deja vu,(非得說「既視感」嗎),意識浮現的一個凸點,提醒一個潛行的環狀運行到站,只是不在原來的月台。輪迴。Come to full circle. 打轉。翻滾。語言中的常用詞,天生個性生成的慣性行為造成的大小不規則形狀反覆,「又」怎麼了的怎麼,堆疊出人生,以時間之刃縱剖,橫切面無一相同又瞬息萬變。
家史二年的三成員,父親母親與長子,在家史七十八年同穴安息,家史最後一章開始。可以放任的循環已無時間容量再放任周行。計時器機心內精緻咬合的大小齒輪,集體推動人生的前進,直到卡卡感出現,銜接點曝光,你終於停頓,審視,回顧,比較,理出一道奇異的脈絡,無關因果,而是我之為我的判斷和選擇,一路走來踩踏出的一道長音,無意中,潛意識裡,埋入下次再見的印象和不知怎麼結尾的感覺,不收邊地延展。